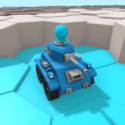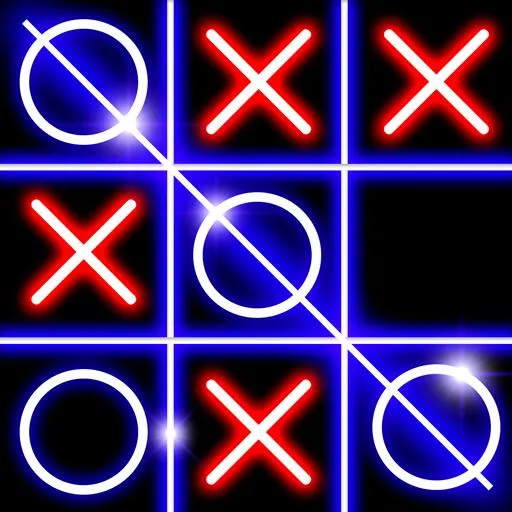摘要
在北魏之前,北方始终没有能正式开始青瓷的生产。目前考古发现的,有限的十六国时期陶瓷生产遗迹都是陶窑窑址,且产品多为瓦当、板瓦、筒瓦甚至灰陶水管道这些“建筑用陶”。这基本说明,在十六国这个政权倏忽而立、又倏忽而灭的时期,各短命割据政权只来得及用陶来建造宫室,还未来得及在日常生活中普及高级陶瓷器,就灭亡了。我们知道,从陶“进化”为瓷,除了原料资源和工艺准备以外,政治相对稳定和经济相对繁荣是必要的外部环境。北方直到北魏均田、汉化并迁都洛阳后,这种外部环境才得以逐步出现。这样,从北魏晚期开始萌芽,至东魏和北齐,北方的青瓷生产终于起步。
第三编 全盛序曲
第一章、新“华夏”与瓷的新变局
第二节、北瓷曙光
一、太和九年
任何政治结构之变革,如果不先做好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之准备,则必然引发大乱。北魏汉化之意识形态改变先行于政治结构改变,上面已详述之。现在,要说一说其经济基础之变革。
孝文帝太和九年也就是公元485年,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以及南北朝史,甚至中国中古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北魏朝廷颁布了《均田令》。《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以下简称《魏书食货志》):
(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
这个“均田令”出现的背景,是北方自“五胡乱华”起经济的崩溃,或者说基本不存在国家经济。因为国家经济需要一个基础,就是田土大部分属于国家或者自耕农,而不是集中于某些势力集团。但是太和九年之前的北方确实不是这样的,《魏书食货志》: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
在这里我们看到,“均田令”之前,北魏的自耕农数量极少,其经济实际也是大领主庄园经济,只不过它的大领主不是南朝的士族,而多为“豪强”,也就是地方豪门和“胡”族军事贵族。而“豪强”们对于农民的征敛,是远大于朝廷对于自耕农的税赋的。这样,孝文帝(更多的是冯太后)面对的经济局面就和当年的曹操一样,必须用战乱腾出来的无主耕地,把农民从豪强手里解放出来。但与曹操采用的“抑豪强”行“民屯”不同,孝文帝(冯太后)采用的是更具历史先进性的方法,就是“均田”,让荫附豪强的农民成为自耕农而不是国家佃农。这样,北魏就具有了国家经济,就可以拥有稳定的中央财政收入。孝文帝要进行的政治结构改革才能有实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底气。
但如果直接实行“均田”,恐怕豪强们会立时起而反抗,则有可能天下为之大乱。孝文帝祖孙确是战术高手,他们在“均田”让天下农民“减负”之前,先反其道而行之,给农民们增了一下负。《魏书食货志》: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
从太和八年开始,北朝的官员们终于领“工资”了,在此之前他们大多过的是“供给制”和自己“抢食”的日子。在没有国家经济的情况下,给这么大一个官僚集团发工资,拿什么发呢?只能增加人民的税赋了,我们看,这一增加可是真不少。但是,这又确实是孝文帝祖孙的一招极有用的“先手”,它让庞大的官僚集团必然地成为中央政府的同盟军。这样,第二年行“均田”时,豪强们就有这个庞大的同盟军来制衡。因此,太和九年开始的“均田”实行得比较平和有效,没给北魏朝廷引起什么乱子。
太和九年的这个“均田令”里,最重要的有以下这么几个内容:
(一)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二)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
(三)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四)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五)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六)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
我们从以上六条“均田令”的核心内容看到:
1、首先是授田的标准。以每一户为授田单位,不但男女主人,而且奴婢,甚至家里自有的耕牛都可以授田。这么“大尺度”的授田标准,无疑说明两点:一是一百多年战乱之后,北方人口锐减,当时朝廷手上的无主耕地极多;二是朝廷急于让每一户农民都拥有尽可能多的土地,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产出,整个国家经济总量就可以迅速增加。
2、政府对于授田户的农业生产内容有极为细致的标准和要求,不按标准生产要受罚。这就说明此时北魏实行了一种“计划经济”,急于按照国家的物资需要统筹农业生产。
3、各户所授之“露田”和“麻田”并不是历史上常说的“永业田”。“露田”是裸露之田,就是不栽树的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基本农田。“麻田”是用来种植苎麻,从而生产麻布的田。这些纯用来生产粮食及麻的田,在北魏时法律上还是国有而非私有的,受田者去世就要交回国家。这样,国家手里的基本农田就能随人口自然更替而有盘量,不至于人口孳长之后国家掌握的田地越来越少,从而无以为继。
4、授予各户用来生产丝织物的“桑田”是“永业田”。但一户之中既然存在了“永业田”的继承,那么在此类田的单户授田总量上,就有可能超出标准或低于标准(因为各户的人口数与男丁比例是可变量),则超出和不足的部分允许自由买卖。这一个“永业田”特例,是因为一直到唐朝后期实行“两税法”之前,各朝赋税太半都是“实物征收”。而所征收的实物中,丝织物是重要部分。太和八年开始给官僚发工资,为此所增加的主要实物税赋就是帛,因此在丝帛的生产上,要让农民有利、有产可图,这样才能保证供应量。保证了丝帛的供应量,中央政府才能按时给官员发工资,政府的运行才能稳定、顺畅。
有了太和九年的这个“均田令”,北魏初步建立了国家经济。于是,三年后它建立了真正的财政体系。
《通典·卷第五·食货五》:
魏令:大率十匹中五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事见于《魏书食货志》记载之太和十年)。
《魏书食货志》:
十二年,诏群臣求安民之术。有司上言:“请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丰年籴贮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一,籴之于民……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民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
这样,北魏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的法令,即地方征收的“调”按以下比例进行分配:公调39%、调外费20%、百官俸禄30%、保险型经费11%——公调就是中央经费、调外费是地方经费、保险型经费用来保障地方上可能遇到的灾害。
太和九年“均田”,国家经济开始初具规模,至太和十年乃能建立财政体系并于十二年完善、确立。于是,到太和十九年,北魏终于在北方恢复了货币体系。《魏书食货志》:
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
有了经济规模、财政体系、货币体系,一个正常的经济环境在北方呈现出来。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有了实现的需求和能力,北朝的手工业和商业就有了繁荣的基础。于是,在被南方独擅了三百年后,瓷器生产这种有赖于经济规模和商业环境的手工业,终于在北方露出了曙光。
二、北朝青瓷
在北魏之前,北方始终没有能正式开始青瓷的生产。目前考古发现的,有限的十六国时期陶瓷生产遗迹都是陶窑窑址,且产品多为瓦当、板瓦、筒瓦甚至灰陶水管道这些“建筑用陶”。这基本说明,在十六国这个政权倏忽而立、又倏忽而灭的时期,各短命割据政权只来得及用陶来建造宫室,还未来得及在日常生活中普及高级陶瓷器,就灭亡了。我们知道,从陶“进化”为瓷,除了原料资源和工艺准备以外,政治相对稳定和经济相对繁荣是必要的外部环境。北方直到北魏均田、汉化并迁都洛阳后,这种外部环境才得以逐步出现。这样,从北魏晚期开始萌芽,至东魏和北齐,北方的青瓷生产终于起步。
就已有的考古发现来说:北朝的青瓷窑址,目前最早可以追溯到的是东魏时期的。但是墓葬考古中,北魏晚期的墓葬里已经有不同于南方青瓷的青瓷器出土。根据南北朝对峙时期的政治状态来看,南朝青瓷的某些技术进入北朝也许还有可能,因为南朝每一次改朝时,总会有边镇刺史、镇将向北朝内附,也会有一些上一朝皇族逃至北朝。但是南朝成品青瓷作为商品有规模、长期性地进入北朝,则可能性较小。因此,北魏晚期墓葬里出土的青瓷,应该是北朝自己生产的。至于北魏的青瓷窑址,相信以后的考古发现会有所证明。总之,把北朝青瓷的萌芽定在北魏晚期还是逻辑可信的。目前已有的北朝青瓷窑址考古发现集中于山东和河北,这些地方的窑址发掘带给了我们很多关于北朝青瓷背后的历史信息。
山东省内的北朝青瓷窑址集中发现于淄博、临沂、枣庄三个地区,也就是东魏、北齐的“青、徐”之地:淄博属于当时的青州;临沂与枣庄属于当时的北徐州。这个地区就是“关东”之核心区,北魏就是征服了这个地区之后才开始走上“中国”之主的道路。这个地区同时也是传统的中原高门士族集中区域。相关考古报告指出:
这个时期的窑址主要有淄博地区的寨里窑、枣庄地区的中陈郝北窑和临沂地区的朱陈窑。窑址所出土器物组合比较简单:有碗、罐、高足盘、盘口壶、杯、盆等。器物造型厚重,胎质粗糙,呈青灰或浅黄色,有气孔和黑点。多见青褐色釉器物,釉汁厚薄不匀,釉面斑驳,釉中有铁锈色斑点,光洁度差,个别有垂釉现象。也有少数青黄色釉器物,釉层较厚,釉汁较匀,有冰裂纹和垂釉。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器物,不但与同时期的南朝青瓷无法相比,就是同三国孙吴时期的南方青瓷相比也大为逊色。著者本身是烧制青瓷的世家,从青瓷工艺角度看,这些出土的北朝青瓷:它们的胎质粗糙,说明当地缺乏优质的瓷土资源,并且修坯工艺落后;它们的釉色从浅黄到清灰到青黄到青褐皆有,说明窑炉内只是偶尔能烧出还原气氛,大部分时间内还是只能烧出氧化气氛;它们的表面有气孔与黑点,说明窑炉内杂质很多,瓷窑没有得到最佳的燃料供应;它们釉汁厚薄不匀,釉面斑驳,说明上釉工艺和修釉工艺极为落后;它们釉中有铁锈色斑点,光洁度差,说明釉水中杂质较多,釉水配方较为原始。综上所述,北朝青瓷的工艺水平比之南朝要落后近三百年,基本处于原始青瓷刚刚迈入青瓷门槛的那个阶段……
但即使是这样原始而粗糙的青瓷,在当时的北朝依然是由最顶级士族使用的。该考古报告指出:
这时期的墓葬,淄博市临淄北朝崔氏墓群发现了三座有明确纪年的东魏、北齐墓,均出土了瓷器。M3墓主人崔混葬于东魏元象元年(538年); MS墓主人崔德葬于北齐天统元年(565年); M12墓主人崔博葬于北齐武平四年(573年)。崔混墓出土的碗和带盖四系罐,与寨里窑出土的同类器物的造型、釉色皆相同。崔德、崔博墓出土的碗和高足盘,与寨里窑的产品大致类似。崔氏墓群是北朝东清河望族崔氏的墓地,在今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距淄川区寨里窑址约30公里,墓中出土的瓷器大部分可能为寨里窑所产。
清河崔氏无疑是北朝最重要的高门士族,但他们也只能使用这种水平很差的青瓷陪葬。从这一点说,比起他们在南朝的士族兄弟来,他们实在是生活质量堪忧。至于北朝那些非高门的庶族,其能否用得上瓷器恐怕都要画个问号。
河北地区的北朝青瓷窑址集中发现于邯郸地区,即现在的邯郸临水镇,紧邻磁县。有关考古报告说:
(所出土)遗物除瓷器外还有较多陶器,瓷器烧造业尚处于创烧期。其特点是:以青釉器为主,釉色青灰。另有少量黑釉器,器物品种较少,以碗为主;另有少量钵、高足盘和长颈瓶等。器物多敦实厚重,底足多平底实圈足。器表除化妆土有无及釉色变化外,仅见少量弦纹。其中,出土的青釉中腹碗,与磁县北齐高润墓和景县隋高潭墓出土的青瓷碗相同;青釉高足盘和青瓷钵,与邢台市顺德路隋代邢窑出土的黄釉或白釉高足盘和敛口钵相同或相近。陶器中的灰陶碗与同期青瓷碗形式相同,红陶浅腹碗,更是北朝晚期墓葬或北朝至唐初遗址中常见的器形。
这个地区在北朝,地缘位置了得:是东魏、北齐的都城邺都所在的司州(首都区)。但是我们看到,它还处于陶、瓷兼烧的阶段,青瓷开始生产的时间是明显晚于山东地区的。这就充分说明,是高氏迁都于邺造就了这个地区的瓷窑。在这里还不是首都的时候,它们应该只是陶窑。是朝廷的到来带来了对青瓷的需求,才把这个地区的陶窑升级成了瓷窑。
上海博物馆藏北齐青瓷刻花莲瓣纹四系罐
综合上面的资料,我们对于北朝青瓷可以做出如下的判定:
(一)北朝青瓷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南朝。因此,南朝青瓷技术向北朝大规模输出应该是不存在的。这也就从一个角度验证了南北朝对峙的一种历史现实,它们之间是比较严格的敌对关系。不存在太多的政治模糊空间,并且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政冷经热”这种状态也不大可能存在。
(二)虽然是北魏的均田与汉化给了北朝青瓷出现的外部环境,但同南朝一样,青瓷一诞生就天然为朝廷与士族服务。由此可见,孝文帝之汉化确实是双刃剑,既让北朝有了成为华夏正朔的历史机会,也让北朝掉进了门阀政治这个历史泥沼。
三、白瓷的萌芽
虽然北朝的青瓷是粗糙而稚嫩的,但北朝的瓷业还是在中国瓷器史上创造了一个不小的成就,就是白瓷萌芽了。关于这一点的主要考古学依据,就是河南安阳于1971年发掘的一座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该墓出土了青釉、白釉、酱釉、彩釉等品种的十三件陶瓷器。对于这座墓里出土的白釉瓷器,在1972年就有专家做出了如下的研究:
范粹墓出土的瓷器,使我们看到了白瓷和青瓷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就是说能看出过渡阶段的特点。隋唐时期的白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白胎(瓷土经过淘洗提炼);第二,白釉,质量高的白釉如白蜡色,白净莹润,质量不太高的白中泛黄或泛青;第三,釉层较青瓷的釉层薄,有的薄到只有青瓷釉层的1/3左右。范粹墓出土的这批瓷器已经初步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胎质洁白、细腻,瓷土经过充分的淘洗提炼;釉子莹润,釉层薄;已经没有北方青瓷灰胎(或灰白胎)、凝厚青釉的特点了。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瓷罐和瓷碗,釉色明显泛青。但总的说来,范粹墓出土的瓷器占主流的是白瓷的特点,但又保持着一些青瓷的痕迹。因此,它清楚地表明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
于是,在30年前撰写的陶瓷史上,就依据这个研究认为:
白瓷是在北朝青瓷的基础上出现的。而它的出现,则是北朝瓷工实现了技术上的一种飞跃,因为他们可以控制釉水里的铁含量,最大限度地把铁含量降低。由于釉水中不再有可以还原出青色的铁元素,因此就烧出了白瓷。
这种结论里有一个很大的逻辑不通之处,非常值得商榷,那就是:北朝这种瓷器的白色是不是一种人工选择。
根据陶瓷史的论断,是因为北朝瓷工对釉水里的金属元素含量进行了人工干预,从而创造了白釉瓷。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北朝的瓷器生产水平必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特别是:既然说白釉瓷来自于对青瓷的釉水干预,那么北朝青瓷的生产必然水平极高,一定是远超南朝的,因为南朝并没有经常性地出现这种白釉瓷。此种论调出现于1972年之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陶瓷史中定论。但是其后,山东、河北的北朝青瓷考古发现却明确告诉我们,北朝之青瓷生产水平是如何的原始。我们很难相信,一个连青瓷釉色都无法稳定控制的瓷器产区,可以同时人工干预釉水里的金属元素,自主决定釉色是青是白。要知道,范粹墓所在的河南安阳和邯郸临水镇的青瓷窑址,处于同一时期的同一地区(都是邺都地区)。那么这同一个时期的同一个地区,又怎么可能出现两种差距悬殊的瓷器生产水平。
因此,对于北朝白釉瓷的出现,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不是人工的选择,而是地理环境的选择。我们说过,瓷器之所以从青瓷起步,是因为铁是自然矿石中最多见的金属元素。青瓷最早出现和发展于南方,很大原因在于南方的矿石中普遍铁元素含量较高。那么,对于青瓷水平低下的北朝出现了白釉瓷,特别是表现为带淡青灰色的白釉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在北方某些瓷窑的所在地,矿土资源中铁含量很少。再加上烧成工艺的极不成熟,未能实现还原气氛,无法有效稳定还原青色。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就偶发性地烧出了近乎白釉的淡青灰色瓷器。之后,隋唐大帝国出现,北方迎来了瓷业的大发展。于是,北方的瓷工对北朝的这种“白瓷”进行了长期的工艺摸索和改进,实现了真正的白釉瓷制作工艺,才使白瓷成为唐、宋以降北瓷的代表。
上海博物馆藏隋白瓷印花双系扁壶
应该说,这样来理解白瓷的祖源才更合乎历史以及工艺学逻辑。但无论如何,北朝出现的这种“白瓷”,确实是北方未来得以成一瓷系,得与南瓷比肩的源头。